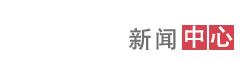竺可桢
一一个可以不参加中科院党组活动的党员副院长,由于周恩来的保护,他没有直接受到暴力冲击。整个“文革”期间,他既没有受到正面批判斗争,也没有遭到抄家之祸。从表面上看,他只是离开了工作(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他的实验室就是大自然,以前他每年都要多次外出,直接考察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变化情况。同时他也从各地科学家不断的汇报资料和成果中,获得大量的信息,作为他认识自然,理解自然的根据。)退守到家中。也许是为了减少一些心头上的重负,他将自己的生活待遇一降再降。“文革”前夕,为了避免脱离群众,不知不觉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经沈雁冰倡导,他和老舍等人联名申请,降低工作标准。没几日,他又觉得光降低工资标准还不足以表现“继续革命”的思想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便和吴有训商量,两家一起采取一系列措施:
(1)减缩工作三分之一上交国家,只领原薪的三分之二;
(2)组织上安排的公务员,由院里另行安排工作,同时辞退家中雇用的保姆;
(3)缩小住房面积,腾出当时儿子和保姆的房间(1976年又腾出了原做卧室的正房和耳房各一间);
(4)不铺地毯、不摆沙发、不挂画饰,家中这些东西,全部交中科院有关部门;
(5)到院里上班或有公务时,和吴有训合乘一辆汽车,到图书馆、情报所查资料时,改乘公共汽车;
(6)把个人私有钢琴赠与科学院芳嘉幼儿园。
经过自我“改造”,到“文革”后期,身患肺气肿的竺可桢所拥有的只是一个仅能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了,他和那些住在建国门或东大桥的居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还要差。他经常要去一里外的粮店买15斤大米,路上要歇上好几次。遇到自己做饭就更麻烦了,他60多岁的太太陈汲常常被街道办事处撵到街上跳忠字舞或参加游行、批判走资派等革命活动,他只好自己在家依着太太的说法,比葫芦画瓢地做家务。竺可桢将自己的待遇一降再降,以至最后像苦行僧一样不断地折磨自己,但这样也丝毫不能减轻他心中的痛苦。
竺可桢无疑承受着另一种也许是更重的痛苦,这种痛苦发源于他的人格和仁爱之心。失去工作的竺可桢,尽管受到特别保护,却也没有闲着,因为他的特殊经历让很多人都瞄上了他,这使得他的家几乎成了来访接待站。每年都有天南海北大量的外调人员拥到他这里。
来找竺可桢调查的人,大体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前后,被清理出来的“特务”、“间谍”、“历史反革命”等。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另一个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因竺可桢是浙江大学校长,因而他的学生或教师、教授,凡是被调查的,一律都是敌对势力的受怀疑对象;另一类是在“三结合”中,两派人员对某人持有不同意见,或想打倒对方,就各自出人员,根据自身的需要,有目的地进行调查。这使得竺可桢每每应接不暇。据统计,竺可桢在“文革”最初的几年里,接待外调人员(多为造反派)一共500多批,最繁忙的是1968年,这一年他就接待了183批外调人员。这种繁琐忙乱的接待,让竺可桢苦不堪言,他曾向朋友发牢骚说:“文革”期间,没做什么事,这事倒成了主要工作了。可是从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的这份独特的工作而心存感念。他知道,每一次来访,每调查一个人,都关系到那个人的命运和生存。来访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同感,就是这个老人的繁琐与谨慎。他总是仔细地翻阅自己几十年来,几乎一天不辍的日记,他要小心地做一些准备(因为他认为时间久远有一些人与事已漫漶不清了)。有鉴于此,他还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有关人物进行整理,编出供本人使用的索引。那些外调人员有个相同的感觉,一来到这个清癯干瘦儒雅的老人这里,他们的热情就会受阻。在这里,他们得不到什么重大线索。那些经过风浪的造反派承认:这个老家伙软硬不吃。你要暗示他“配合”的话,他便一声不吭,似不懂你的意思,你若施以暴力威胁的话,他也一声不吭,就像坚守信仰的教徒一样,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一副安然超度的样子。

竺可桢小心谨慎地应付着一批又一批外调人员,用他独特的方式保护着他当年的学生、教授和朋友。
文革浩劫过后,各种纪念他的活动从未间断,学术界相继编辑出版了《竺可桢文集》、《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论文报告集》、《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五卷本的《竺可桢日记》和多种版本的竺可桢传记。
中国科学院设立了“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浙江大学设有“竺可桢奖学金”和“中学竺可桢教书育人奖”。浙江上虞县东关镇辟有“竺可桢故居陈列馆”,浙江绍兴市气象局在国家气象局的支持下辟设了“竺可桢纪念馆”,江苏省气象局在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旧址辟设了“藕舫堂”。浙江大学校园中和中国科学院917大楼前竖起了竺可桢铜像。中国人民邮政发行了包括竺可桢在内的当代中国科学家纪念邮票。学术界同人发起成立了“竺可桢研究会”。多年以来,由个人在各种学术刊物和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纪念和回忆文章,就举不胜举了。
竺可桢的《沙漠里的奇怪现象》被收录在苏教版语文书八年级下中,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课文《大自然的语言》改写自《一门丰产的科学——物候学》。
竺可桢的第一任妻子张侠魂是当时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关于他们的婚姻,《吴宓自编年谱》中提到:“张默君(张侠魂的姐姐)来波城(波士顿),为妹择婿,得竺君‘年少美才’,甚喜。商谈结果,竺君与张妹订婚。竺君今年回国,任国立东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与张妹结婚。虽未见面而订婚、结婚,结果亦甚圆满。”
竺可桢功成名就,张侠魂功不可没。后来,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与张家的支持也有一定的关系。张侠魂出身望族,毕业于上海女校,湖南人,性格活泼开朗,文章书法都很有功底。婚后,张侠魂随竺可桢来到武汉。从此,竺可桢结束了在食堂、饭馆吃饭的单身生活。
1922年与夫人张侠魂及子女合影
1938年暑假,由于日寇入侵,浙江大学西迁,竺可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迁校工作上。7月23日,在桂林考察的竺可桢接到夫人张侠魂患了痢疾的电报,随后,竺可桢返回泰和,在浙大长堤上见到等候在那里的大女儿竺梅,竺梅说妈妈的病好些了;当竺可桢听到“衡(幼子)没了”,眼泪簌簌流下。
他回家后看到张侠魂因患痢疾病卧在床,已经病危了。竺可桢强忍悲痛,抚慰夫人。张侠魂和竺衡得的是痢疾,由于战争,医疗条件太差,8月3日上午,张侠魂不幸逝世。半月之内,竺可桢接连丧妻失子,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竺可桢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其中有依陆游《沈园》诗原韵吟成的悼亡诗: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从中可以看出竺可桢对妻子的一片深情。每年的8月3日,竺可桢总要设家祭纪念张侠魂,十几年后依然如此。
张侠魂去世后,多位亲友见竺校长公务繁忙,子女年幼,劝他早日续弦。其中物理学教授丁绪贤的太太陈淑想把她的堂妹陈汲介绍给竺校长。陈汲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生,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的胞妹。陈汲的形象和气质,在新月派文人的笔下有记录,胡适对陈汲的印象深刻。
与陈汲在遵义结婚
1939年9月18日,竺可桢与陈汲登上峨眉山金顶,热烈相拥,喜定终身。下山后,于9月21日晚在嘉定饭店请订婚宴。一年之余的相恋终于水到渠成,1940年3月15日,举行婚礼。陈汲生性贤惠,品貌端庄,只因陈源、陈洪两个哥哥长年在外,她要照顾双亲二老,才迟迟于36岁时成婚。
1940年12月14日,他们有了爱情之果,生一女孩,小名毛毛,大名竺松。此后几十年,陈汲辅佐竺可桢,关爱学生,抚育子女,直至走完生命的旅程。
(1)减缩工作三分之一上交国家,只领原薪的三分之二;
(2)组织上安排的公务员,由院里另行安排工作,同时辞退家中雇用的保姆;
(3)缩小住房面积,腾出当时儿子和保姆的房间(1976年又腾出了原做卧室的正房和耳房各一间);
(4)不铺地毯、不摆沙发、不挂画饰,家中这些东西,全部交中科院有关部门;
(5)到院里上班或有公务时,和吴有训合乘一辆汽车,到图书馆、情报所查资料时,改乘公共汽车;
(6)把个人私有钢琴赠与科学院芳嘉幼儿园。
经过自我“改造”,到“文革”后期,身患肺气肿的竺可桢所拥有的只是一个仅能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了,他和那些住在建国门或东大桥的居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还要差。他经常要去一里外的粮店买15斤大米,路上要歇上好几次。遇到自己做饭就更麻烦了,他60多岁的太太陈汲常常被街道办事处撵到街上跳忠字舞或参加游行、批判走资派等革命活动,他只好自己在家依着太太的说法,比葫芦画瓢地做家务。竺可桢将自己的待遇一降再降,以至最后像苦行僧一样不断地折磨自己,但这样也丝毫不能减轻他心中的痛苦。
竺可桢无疑承受着另一种也许是更重的痛苦,这种痛苦发源于他的人格和仁爱之心。失去工作的竺可桢,尽管受到特别保护,却也没有闲着,因为他的特殊经历让很多人都瞄上了他,这使得他的家几乎成了来访接待站。每年都有天南海北大量的外调人员拥到他这里。
来找竺可桢调查的人,大体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前后,被清理出来的“特务”、“间谍”、“历史反革命”等。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另一个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因竺可桢是浙江大学校长,因而他的学生或教师、教授,凡是被调查的,一律都是敌对势力的受怀疑对象;另一类是在“三结合”中,两派人员对某人持有不同意见,或想打倒对方,就各自出人员,根据自身的需要,有目的地进行调查。这使得竺可桢每每应接不暇。据统计,竺可桢在“文革”最初的几年里,接待外调人员(多为造反派)一共500多批,最繁忙的是1968年,这一年他就接待了183批外调人员。这种繁琐忙乱的接待,让竺可桢苦不堪言,他曾向朋友发牢骚说:“文革”期间,没做什么事,这事倒成了主要工作了。可是从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的这份独特的工作而心存感念。他知道,每一次来访,每调查一个人,都关系到那个人的命运和生存。来访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同感,就是这个老人的繁琐与谨慎。他总是仔细地翻阅自己几十年来,几乎一天不辍的日记,他要小心地做一些准备(因为他认为时间久远有一些人与事已漫漶不清了)。有鉴于此,他还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有关人物进行整理,编出供本人使用的索引。那些外调人员有个相同的感觉,一来到这个清癯干瘦儒雅的老人这里,他们的热情就会受阻。在这里,他们得不到什么重大线索。那些经过风浪的造反派承认:这个老家伙软硬不吃。你要暗示他“配合”的话,他便一声不吭,似不懂你的意思,你若施以暴力威胁的话,他也一声不吭,就像坚守信仰的教徒一样,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一副安然超度的样子。

竺可桢小心谨慎地应付着一批又一批外调人员,用他独特的方式保护着他当年的学生、教授和朋友。
文革浩劫过后,各种纪念他的活动从未间断,学术界相继编辑出版了《竺可桢文集》、《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论文报告集》、《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五卷本的《竺可桢日记》和多种版本的竺可桢传记。
中国科学院设立了“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浙江大学设有“竺可桢奖学金”和“中学竺可桢教书育人奖”。浙江上虞县东关镇辟有“竺可桢故居陈列馆”,浙江绍兴市气象局在国家气象局的支持下辟设了“竺可桢纪念馆”,江苏省气象局在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旧址辟设了“藕舫堂”。浙江大学校园中和中国科学院917大楼前竖起了竺可桢铜像。中国人民邮政发行了包括竺可桢在内的当代中国科学家纪念邮票。学术界同人发起成立了“竺可桢研究会”。多年以来,由个人在各种学术刊物和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纪念和回忆文章,就举不胜举了。
竺可桢的《沙漠里的奇怪现象》被收录在苏教版语文书八年级下中,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课文《大自然的语言》改写自《一门丰产的科学——物候学》。
两任太太
竺可桢的第一任妻子张侠魂是当时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关于他们的婚姻,《吴宓自编年谱》中提到:“张默君(张侠魂的姐姐)来波城(波士顿),为妹择婿,得竺君‘年少美才’,甚喜。商谈结果,竺君与张妹订婚。竺君今年回国,任国立东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与张妹结婚。虽未见面而订婚、结婚,结果亦甚圆满。” 竺可桢功成名就,张侠魂功不可没。后来,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与张家的支持也有一定的关系。张侠魂出身望族,毕业于上海女校,湖南人,性格活泼开朗,文章书法都很有功底。婚后,张侠魂随竺可桢来到武汉。从此,竺可桢结束了在食堂、饭馆吃饭的单身生活。
1922年与夫人张侠魂及子女合影
1938年暑假,由于日寇入侵,浙江大学西迁,竺可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迁校工作上。7月23日,在桂林考察的竺可桢接到夫人张侠魂患了痢疾的电报,随后,竺可桢返回泰和,在浙大长堤上见到等候在那里的大女儿竺梅,竺梅说妈妈的病好些了;当竺可桢听到“衡(幼子)没了”,眼泪簌簌流下。
他回家后看到张侠魂因患痢疾病卧在床,已经病危了。竺可桢强忍悲痛,抚慰夫人。张侠魂和竺衡得的是痢疾,由于战争,医疗条件太差,8月3日上午,张侠魂不幸逝世。半月之内,竺可桢接连丧妻失子,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竺可桢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其中有依陆游《沈园》诗原韵吟成的悼亡诗: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从中可以看出竺可桢对妻子的一片深情。每年的8月3日,竺可桢总要设家祭纪念张侠魂,十几年后依然如此。
张侠魂去世后,多位亲友见竺校长公务繁忙,子女年幼,劝他早日续弦。其中物理学教授丁绪贤的太太陈淑想把她的堂妹陈汲介绍给竺校长。陈汲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生,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的胞妹。陈汲的形象和气质,在新月派文人的笔下有记录,胡适对陈汲的印象深刻。
与陈汲在遵义结婚
1939年9月18日,竺可桢与陈汲登上峨眉山金顶,热烈相拥,喜定终身。下山后,于9月21日晚在嘉定饭店请订婚宴。一年之余的相恋终于水到渠成,1940年3月15日,举行婚礼。陈汲生性贤惠,品貌端庄,只因陈源、陈洪两个哥哥长年在外,她要照顾双亲二老,才迟迟于36岁时成婚。
1940年12月14日,他们有了爱情之果,生一女孩,小名毛毛,大名竺松。此后几十年,陈汲辅佐竺可桢,关爱学生,抚育子女,直至走完生命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