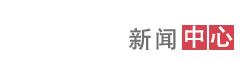陈焕镛
院长孙仲逸,将农学院科学馆前原林学系的苗圃拨给该所。陈焕镛老师锐意经营,每日雇请临时工数十人,亲自指挥,严寒酷暑,风雨无间,栽植花圃树木,亲自开辟桂林植物园。
“他不是一个好父亲”(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与陈都女士的访谈整理。陈焕镛院士的女儿陈都女士现就职于某国际保险公司)

我爸几乎不过问家里的事情,大大小小都是我妈妈一人操持。我妈原是父亲家里的工人,我大妈(爸爸的第一个妻子唐直珍,听长辈说大妈是富家小姐,跟父亲还算门当户对)过世后,我妈就跟我爸结了婚。我妈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一直站在爸爸背后打理家中的一切,从来没让我爸操过心,我爸才可能潜心搞研究。
我的童年是苦难的,从懂事之日起,就开始担惊受怕。因为我爸是“文化汉奸”、“里通外国”,所以没有人敢跟我同桌,没有人敢跟我说话。长大了,我都一直把那段苦难的岁月压得紧紧的,不想跟任何人提起,我试着忘记它。原来我被压抑得非常内向,不爱跟人说话,现在我很乐观积极。
我在研究所工作了18年,别人介绍我时都说“这位是陈老的女儿”。好像再多的努力与汗水都难以体现自己的价值,我只有选择离开父亲的光环。后来我到了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如今已有六年了,我觉得很满意,做得也很开心。父亲给我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学会自立”。
“他是一个特别专的人”(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与张宏达教授的访谈整理。张宏达,中山大学教授,1914年出生,193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曾在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担任陈焕镛的助手)

有一次,我发现了属于“金缕梅”下面的一个新属,而且那是我第一次搞研究,我很激动地找到陈老,他很兴奋地拍着我肩膀说:“你真走运!”因为那个标本陈老用过,但陈老自己也没有发现。我想跟陈老一起发表这个新属,陈老说:“你发现的,当然你发表!”后来在论文中我便将此新属命名为“陈氏木”,以表达我对陈老的尊敬。
陈老很关心所里的员工,他经常请我们出去吃饭,在饭桌上谈笑风生。他其实是个很风趣的人,只是搞起研究来,就很少说话。
他人评价
“他不是一个好父亲”(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与陈都女士的访谈整理。陈焕镛院士的女儿陈都女士现就职于某国际保险公司)
1964年,陈焕镛在北京与家人合影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优秀的植物学家,但不是一个好父亲,他的时间、精力都投到了研究中,好像很少有空来管过我跟哥哥。也许我爸爸心底还是爱我的,只是他实在没有时间来表露,有一件事情印象很深——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跟他一起散步,刚下过雨,我穿着雨鞋,路旁有很深的草,还有积水,我爸一定要让我把雨鞋倒过来抖一抖再穿,我偏不听,当时他很生气。后来我才明白,爸爸在野外采集标本时,雨鞋里经常会爬进蛇、虫子什么的。很多年以后,我才懂得爸爸当时的心情。我爸几乎不过问家里的事情,大大小小都是我妈妈一人操持。我妈原是父亲家里的工人,我大妈(爸爸的第一个妻子唐直珍,听长辈说大妈是富家小姐,跟父亲还算门当户对)过世后,我妈就跟我爸结了婚。我妈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一直站在爸爸背后打理家中的一切,从来没让我爸操过心,我爸才可能潜心搞研究。
我的童年是苦难的,从懂事之日起,就开始担惊受怕。因为我爸是“文化汉奸”、“里通外国”,所以没有人敢跟我同桌,没有人敢跟我说话。长大了,我都一直把那段苦难的岁月压得紧紧的,不想跟任何人提起,我试着忘记它。原来我被压抑得非常内向,不爱跟人说话,现在我很乐观积极。
我在研究所工作了18年,别人介绍我时都说“这位是陈老的女儿”。好像再多的努力与汗水都难以体现自己的价值,我只有选择离开父亲的光环。后来我到了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如今已有六年了,我觉得很满意,做得也很开心。父亲给我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学会自立”。
“他是一个特别专的人”(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与张宏达教授的访谈整理。张宏达,中山大学教授,1914年出生,193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曾在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担任陈焕镛的助手)

陈焕镛的中英文手稿
1939年是我毕业前的最后一年,陈老担任我们植物系的系主任。他是一个特别“专”的人,大多数时间在标本室里搞研究,对在学术上特别认真、特别投入的学生常常刮目相看。他定下了许多新种和新属,从不急于发表,经常反复推敲求证,以观光木属为例,从发现到正式发表经过了十几年的观察。写作学术论文,必每字每句反复斟酌,有疑难处,必博考群书,方才命笔。每写成一篇论文经三四稿,甚至五次六次修改,然后定稿,从不草率行事。有一次,我发现了属于“金缕梅”下面的一个新属,而且那是我第一次搞研究,我很激动地找到陈老,他很兴奋地拍着我肩膀说:“你真走运!”因为那个标本陈老用过,但陈老自己也没有发现。我想跟陈老一起发表这个新属,陈老说:“你发现的,当然你发表!”后来在论文中我便将此新属命名为“陈氏木”,以表达我对陈老的尊敬。
陈老很关心所里的员工,他经常请我们出去吃饭,在饭桌上谈笑风生。他其实是个很风趣的人,只是搞起研究来,就很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