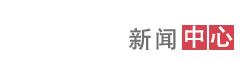张香桐
铁炉子,长长的铁皮烟管通向窗外。显然是久未使用的过时之物了,但主人从来没动过拆掉的心思。“已经有好几只麻雀在里面做了窝,还孵出了小麻雀。拆掉了炉子,它们住到哪里去?”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冯林音是张香桐的女弟子,先生的绅士风度至今让她难以忘怀,那年教师节期间,她参加报社和上海教育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寻找恩师,感念师恩”活动时,讲述了一个细节,“某天,我推着自行车在研究所门口遇见准备回家的张先生。见着我,先生又回过头陪我往所里走,并为我按住电梯的按钮。”不止一个人记得,张先生是“女士优先”的严格实践者:如与女士同行,进门时他必定先一步为女士开门。遇有记者采访,结束采访,起身话别,张先生也会跟着站起来,虽然步子有些摇摆,可他坚持要将记者送到门口。
在自己身体上做试验
针灸起源于中国,如何将这种传统医学技术纳入现代医学,是神经生理科学家的责任。多少年来,正确揭示针刺镇痛现象的机理一直是对神经生理学家的一个挑战。
为了获得针刺麻醉的第一手资料,以真切了解针刺镇痛的生理机制,1965年5月,当时已年近六旬的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果断地向上海市卫生主管部门申请,要求在自己身体上进行一次不用任何麻醉药物、只靠针刺来镇痛的左侧肺切除的模拟手术。申请被批准后,张香桐实实在在真切地体验了一次针刺镇痛模拟手术的全过程。
那天张香桐身上足足扎了60多根银针。模拟手术后很长一段时间,被针刺过的上、下肢仍不能自由活动,左手几乎完全丧失了运动功能,甚至连打领带、扣扣子都不行。张香桐的老保姆在一旁怜悯地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去自讨这份儿苦吃?”张香桐却不以为然地笑道:“以一人之痛,可能使天下人无痛,不是很好么?”通过实践与体验,张香桐真切地认识到针刺镇痛是两种不同感觉传入中枢神经系统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张香桐研究团队所取得的揭示针刺镇痛机理的科研成果,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在美国兴起了针灸热,日本、瑞典等国也纷纷邀请他们去作报告。张香桐本人则相继被聘为巴拿马麻醉学会名誉会员、比利时皇家医学院外籍院士、国际痛研究协会荣誉会员等。该项科研成果也于1978年、1980年分别荣获全国科技大会成果奖、中科院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及1980年度茨列休尔德奖。
更值得一提的是,张香桐科研团队的针刺镇痛科研成果还得到了李约瑟博士的认可,在他与鲁桂珍博士共同撰写的《天针——针灸历史与理论》付梓之前,执意要张香桐作中文题词,刊于卷首。张香桐却以“佛头置粪,未敢造次”予以婉辞,但李约瑟执意索词,张香桐只好从命。这就是当代著名科学史家对张香桐科研团队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与赞许,令张香桐感到无限欣慰。提及此事,张香桐兴奋地说:“天下没有任何事比自己的工作被同行专家所引述并加以赞许,更令人感到高兴了!”
孜孜不倦
大器晚成的张香桐能取得这样的学术地位与其孜孜以求专注做事的风格有很大的关系。给吴建屏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张先生专注科学研究的执著精神:张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搞他的生理学科学研究,没有什么事能分散他的精力,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仍坚持做到这一点,在“牛棚”里还能抓紧时间写科普读物,《癫痫答问》一书就是在“牛棚”里完成的。
进入耄耋之年后的张香桐理应颐享天伦之乐,然而他老骥伏枥,依然不辞辛劳,充满青春之锐气。只要身体没有不适,几乎天天早晨按时出现在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办公室。读论文、会友人,或写出访随笔,或写科普文稿,或编往事回想……忙得不亦乐乎,生活得有滋有味。百岁老人的心中仍充满生命之欢乐,事业之诱惑;他有诗人般的激情,有童稚般的纯真。
张香桐虽然肌肤衰老,但对科学事业的执著与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因为他明白: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唐必致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生命又是如此短促,“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争分夺秒!”这是令张香桐充溢勇锐之气的源泉。
青春对于张香桐是永存的,因为他有“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情感”。
2005年12月6日,当上海科普作家协会首批荣誉会员证书送至99岁高龄的张香桐手中时,他兴奋地在签收本上挥就了“科普万岁”四个遒劲的大字。
《刺猬的一种听觉反射》(1935)
《猴运动皮层内肌肉的局部代表性》(1947)
《直接电刺激大脑皮层产生的皮层神经原树突电位》(1951)
《大脑皮层神经原的顶树突》(1952)
《皮层诱发电位的相互影响》(1953)
《光刺激引起的蟾蜍小脑前庭神经原的电活动》(1959)
《针刺镇痛的神经生理学解释》(1980)
他在1947~1949年间提出的关于大脑皮层运动区的肌肉局部代表性的工作和用逆行刺激锥体束的方法研究锥体束起源的工作,至今仍被引用。
1950年发表的《皮层-丘脑之间循回性的重复放电》一文,探讨了脑电的产生机制,得到较高的评价。他所发现的光强化脑兴备性的现象曾被人称为“张氏效应”。
1965年后,他从事针刺镇痛及痛觉机制的研究,认为针刺镇痛是两种感觉传入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冯林音是张香桐的女弟子,先生的绅士风度至今让她难以忘怀,那年教师节期间,她参加报社和上海教育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寻找恩师,感念师恩”活动时,讲述了一个细节,“某天,我推着自行车在研究所门口遇见准备回家的张先生。见着我,先生又回过头陪我往所里走,并为我按住电梯的按钮。”不止一个人记得,张先生是“女士优先”的严格实践者:如与女士同行,进门时他必定先一步为女士开门。遇有记者采访,结束采访,起身话别,张先生也会跟着站起来,虽然步子有些摇摆,可他坚持要将记者送到门口。
在自己身体上做试验
针灸起源于中国,如何将这种传统医学技术纳入现代医学,是神经生理科学家的责任。多少年来,正确揭示针刺镇痛现象的机理一直是对神经生理学家的一个挑战。
为了获得针刺麻醉的第一手资料,以真切了解针刺镇痛的生理机制,1965年5月,当时已年近六旬的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果断地向上海市卫生主管部门申请,要求在自己身体上进行一次不用任何麻醉药物、只靠针刺来镇痛的左侧肺切除的模拟手术。申请被批准后,张香桐实实在在真切地体验了一次针刺镇痛模拟手术的全过程。
那天张香桐身上足足扎了60多根银针。模拟手术后很长一段时间,被针刺过的上、下肢仍不能自由活动,左手几乎完全丧失了运动功能,甚至连打领带、扣扣子都不行。张香桐的老保姆在一旁怜悯地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去自讨这份儿苦吃?”张香桐却不以为然地笑道:“以一人之痛,可能使天下人无痛,不是很好么?”通过实践与体验,张香桐真切地认识到针刺镇痛是两种不同感觉传入中枢神经系统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张香桐研究团队所取得的揭示针刺镇痛机理的科研成果,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在美国兴起了针灸热,日本、瑞典等国也纷纷邀请他们去作报告。张香桐本人则相继被聘为巴拿马麻醉学会名誉会员、比利时皇家医学院外籍院士、国际痛研究协会荣誉会员等。该项科研成果也于1978年、1980年分别荣获全国科技大会成果奖、中科院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及1980年度茨列休尔德奖。
更值得一提的是,张香桐科研团队的针刺镇痛科研成果还得到了李约瑟博士的认可,在他与鲁桂珍博士共同撰写的《天针——针灸历史与理论》付梓之前,执意要张香桐作中文题词,刊于卷首。张香桐却以“佛头置粪,未敢造次”予以婉辞,但李约瑟执意索词,张香桐只好从命。这就是当代著名科学史家对张香桐科研团队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与赞许,令张香桐感到无限欣慰。提及此事,张香桐兴奋地说:“天下没有任何事比自己的工作被同行专家所引述并加以赞许,更令人感到高兴了!”
孜孜不倦
大器晚成的张香桐能取得这样的学术地位与其孜孜以求专注做事的风格有很大的关系。给吴建屏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张先生专注科学研究的执著精神:张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搞他的生理学科学研究,没有什么事能分散他的精力,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仍坚持做到这一点,在“牛棚”里还能抓紧时间写科普读物,《癫痫答问》一书就是在“牛棚”里完成的。
进入耄耋之年后的张香桐理应颐享天伦之乐,然而他老骥伏枥,依然不辞辛劳,充满青春之锐气。只要身体没有不适,几乎天天早晨按时出现在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办公室。读论文、会友人,或写出访随笔,或写科普文稿,或编往事回想……忙得不亦乐乎,生活得有滋有味。百岁老人的心中仍充满生命之欢乐,事业之诱惑;他有诗人般的激情,有童稚般的纯真。
张香桐虽然肌肤衰老,但对科学事业的执著与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因为他明白: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唐必致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生命又是如此短促,“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争分夺秒!”这是令张香桐充溢勇锐之气的源泉。
青春对于张香桐是永存的,因为他有“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情感”。
2005年12月6日,当上海科普作家协会首批荣誉会员证书送至99岁高龄的张香桐手中时,他兴奋地在签收本上挥就了“科普万岁”四个遒劲的大字。
张香桐-主要著作
《刺猬的一种听觉反射》(1935)《猴运动皮层内肌肉的局部代表性》(1947)
《直接电刺激大脑皮层产生的皮层神经原树突电位》(1951)
《大脑皮层神经原的顶树突》(1952)
《皮层诱发电位的相互影响》(1953)
《光刺激引起的蟾蜍小脑前庭神经原的电活动》(1959)
《针刺镇痛的神经生理学解释》(1980)
他在1947~1949年间提出的关于大脑皮层运动区的肌肉局部代表性的工作和用逆行刺激锥体束的方法研究锥体束起源的工作,至今仍被引用。
1950年发表的《皮层-丘脑之间循回性的重复放电》一文,探讨了脑电的产生机制,得到较高的评价。他所发现的光强化脑兴备性的现象曾被人称为“张氏效应”。
1965年后,他从事针刺镇痛及痛觉机制的研究,认为针刺镇痛是两种感觉传入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