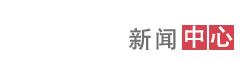林同济
了解决这一冲突,将民族主义所必须的儒家入世传统、尼采的生命强力意志和道家的精神自由整合在同一个人格之中,林同济将道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道家的原初形态:“叛逆加隐士”。中国人的潜意识中都有道家的反叛和退隐意识,不管他是否真的叛逆还是退隐。“道家信徒之所以隐,是因为他藐视一切;但这种藐视不带痛苦成份,他是兴高采烈的退隐的”。隐士所追求的是中国山水画的境界,那种“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境地,这种艺术给人的最大满足在于它的泛神式的宁静”,中国的道家徒正是通过山水画而使自由王国永存。显然,沉湎于自然超越境界的林同济最希翼的,是当这样一个自由自在的叛逆式隐士。但他知道,在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国年代,那是过份的奢望,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说一般中国人是道家徒,实际上他们通常是以第二种类型表现出来的,那就是“流氓”。在道家看来,一个人内心体验可以与他的外部行为区别开来,因此广大的“流氓”虽然内心有自己的价值观,但依然高高兴兴地从众,随波逐流。或者倒过来说,“尽管每一个中国人都继承了儒家的无数繁文缛节,他的心灵仍像空中的飞鸟一样自由”。但这样的“流氓”是为林同济所不屑的。于是,林同济提出了道家人格的第三种类型:“回归主义者”:
这样的道家徒在断然出世后又决定重返社会。他曾经批判自我和所有形式,带着火燃尽后的余灰退隐山间;现在又像虔诚的斗士一样高举形式的火把冲进山谷。经过大胆的否定之否定,这位道家信徒用意志力使自己成为最积极的人。回归主义道家信徒是中国文化所能产生的最高层次的人格。在中国人眼中,他身为道家却为儒家思想奋斗,是最伟大的政治家。30
就这样,林同济通过将儒家与道家、尼采与庄子的结合,展现了一幅道家回归主义者的悲壮人格。这种入世的、战斗的道家,表面看起来与儒家无异,但他的内心充满悲凉,知道一切终究是空,一场空。但他以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存在主义精神,唱着《福者之歌》中的著名词句:“让我来做这一切,我心系永恒,无所企盼。我说:‘这不是我的’,无所悲哀,准备战斗”,坚定地前行,不在意成功或失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31
从提倡尼采式的“战士式人格”,到认同道家的回归主义,不过几年功夫。在无情岁月之中,林同济从意气风华的青年步入了历经风雨的中年。他不再相信理想的实在,已经悟透了人生原是一场空,按照他的内心所愿,本该乘风而去,退隐山林,融入大自然的怀抱。但他心有不忍,依然怀着虚无的理想,在人世间奋斗。从外表看来,人们都会以为他是一个再标准不过的儒家徒,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内心是道家的,姿态是尼采的。他以尼采补庄子,遂成为独特的道家回归主义人生。这样的人生,既参透“苍天”,又听从“大地”的召唤,以悲壮的战斗姿态,将“天”“地”沟通。
时代的变化令人晕眩,偌大的中国已经没有林同济的位置。《战国策》是办不成了,在大银行家陈光甫的支持下,他在上海办了一个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不再期望速战速决的胜利,而是相信持久的渗透力量。尼采式的“激扬四射、压倒一切”的戏剧人生,变为中国道家式的以柔克刚,以一种“大自然般的泛神节拍,不急不缓,永不停息”。321945年以后的林同济,有多次到国外长期任教的机会,临解放以前,父亲也劝他出走海外,但林同济怀着道家回归主义的信念,还是留了下来。没有想到的是,他需要“大地”,但“大地”并不需要他。他只能在大学里面教英文,研究莎士比亚。即便如此,政治运动的风暴也没有放过他,让他当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后半生的生活是凄凉、孤独的,只有在中国山水画和中国古典诗词中,他才稍稍找到一点自由,那种心灵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快乐。
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林同济才重新看到了希望,他的激情又重新涣发了。整整三十年之后,林同济重新访问美国,他在自己的母校伯克利作了三场演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报告,是他毕其一生,对中国思想精髓的研究总结。在这篇他一生中最后的文章中,林同济谈的主题是“天”与“人格”。他告诉西方同行,中国人的思想不止一个人文主义,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人就在为人文主义寻找一个超越的基础,儒家、墨家和道家,都很重视“天”,重视人与宇宙、自我与整体的关系,中国人的心灵一直在探索着一种宇宙的和谐统一,我们可以把中国的人文主义称为宇宙的人文主义。然而,对宇宙的探索,归根结底是对人格的寻找。在中国,重要的是人格,人格是中国思想的精髓,是它的终极关怀所在。“它不仅要与社会融为一体化,也要与宇宙融为一体。最根本的东西是宇宙。人格是人性与超人性的综合。”林同济最后坚定地说:
如果你问在中国人眼中,人到底是什么?关于人的唯一的定义是:人就是他自身所认同的价值。——价值是与宇宙相协调的,宇宙中包含了仁爱和变化,永远在创造,在繁衍。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你将自己和宇宙联结起来之后,你就使自己变得神圣了,你承诺对宇宙的终极忠诚。你与上帝而不是与牧师合二为一。
这就是中国人的方式。
两天以后,过于兴奋和疲劳的林同济,突发心脏病,在旧金山去世。这篇演讲,也成为了他的临终箴言。
从竞争的民族主义到尼采式的战士式人格,最后回归与宇宙的“天人合一”,林同济一步步从历史走向哲学,再归皈宗教,从凡俗走向神圣,从尼采走向宇宙神。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丰富而紧张的心灵,在其中,西方的尼采与中国的庄子、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超脱、国家的集体目标与个人的生命创造,如何奇妙又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相互激荡,相互渗透。世俗与神圣的错位、“天”与“地”的紧张、功利与价值的冲突,这一切都构成了林同济异常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样的内心紧张,一直到晚年,当他参悟人生,找到宇宙与人格的同一性的时候,拥有某种中国式的自然宗教情感的时候,他才慢慢平息下来。他坚信,自然与人,宇宙与人格是无法分离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在宇宙与人之间的所有中介物,如民族、国家等等,一下变得无足轻重。这并不意味着林同济不再关心国家的命运,而仅仅是证明,民族主义并非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价值和关怀所在。在一个以力为中心的战国年代,林同济为建立一个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民族国家呼吁过,但他内心所希翼的,却是一个自然的、审美的、宇宙与人心和谐共处的世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一种相信宇宙与自我共在的自然宗教。假如没有这样的超越意识,现代中国的思想,将浅薄得多、无趣得多。林同济以自己的心路历程,印证了中国人心灵的丰富和复杂,从他这里,可以丈量出现代中国思想的某种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