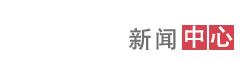王缉思
院学者的文章,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社科院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地位独特,除了拥有一批重要学者之外,其研究所设置也是国内最为齐全的。它的八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几乎囊括了所有世界经济问题。显然,学者构成还有一个年龄层面。本书作者的年龄从三十多岁(比如讨论跨国公司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余万里)到近七十岁的都有。毋庸讳言,年龄跨度的大小与兼收并蓄密切相关。从来源看,本卷辑入的文章主要取自《国际经济评论》、《世界经济》和《世界经济与政治》三份刊物。集中取材于此的主要理由,主要在于这几份杂志具备较好的代表性。
第四是叙述或研究方法。整体上看,世界经济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现代经济学发展很快,博弈论、计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等,均已成为经济学家广泛接受的理论基础和运用的分析工具。特别是在今天,经济学分析往往涉及较为艰深的数学语言,理论性和技术性很强,远非普通读者稍下功夫便可掌握。考虑到本书面对的广大读者对它们可能不太熟悉,同时也为了保证本卷叙事风格与本套丛书的其它七卷相协调,故我对一些很有深度、同时数学或计量分析也非常漂亮的著作不得不忍痛割爱。在保持专业性的同时尽可能回避具有复杂数学推导和计量分析,从而各篇文章具有尽可能强的可读性,是我在挑选编辑过程中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忠实于原文乃第五个标准。总体来看,除了按照丛书要求调整了格式并对各文中明显的疏漏稍作整饬外,我几乎完全保留了各篇文章的本来面目,未作任何增添或删改。这样做,一则是出于对作者的尊重;再则也是为了让本卷文字能够真切地反映出中国学者在这十年之中认知世界经济的心路历程,从而让本书富含更多的历史感。依照今天的眼光看,原文中的有些观点也许并不完全正确,当时做出的一些推断和预测也已经被后来的发展所证伪。将“谬误”和“错判”原封不动地在书中展示,在我看来丝毫不损害作者之声誉。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人非圣贤,还在于实事求是之精神,更在于科学的历史在相当意义上讲无非是能者所犯错误的历史。无论正确与错误,本书力求向世人展示,有这么一批真诚的学者,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认真地思考过,书写过。这或许才是真正的意义。
最后一个标准是落脚点为中国。虽说本卷的主题是中国学者看世界,但他们是戴着中国的眼镜去看世界的,换言之,他们在看世界的同时,心里想的只能是、也必须是中国。从相当意义上讲,对中国人来说,世界只有和中国联系在一起时才具有意义。有意识地收集那些涉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文章,自然也会带来一些编辑上的麻烦,比如说,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逻辑去编排章节。为了突出以中国为落脚点,我专辟“中国与世界”篇。但涉及中国的文章过多,显然不能将其全部归入此篇。面对此困境,我不得不做些技术处理,把与全球化有关的文章(如朱民谈全球失衡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均归入“全球视野”篇,把侧重讨论发展道路和理论性略强的文章(如何秉孟等谈新自由主义问题)放进“理念与思潮”篇。尽管深知顾此失彼难免会对全书的逻辑造成一定的损害,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反观整个编纂过程,对内容的取舍和对作者构成的设计是我用心最甚的环节。中国学者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内的成果之多可谓卷帙浩繁,而我的工作很可能是挂一漏万,错过佳篇力作在所难免。为人作嫁可算善举,代人受过也可一笑泯之,但是若因为自己编辑失当而误导广大读者抑或“泱及”作者本人,那却是我从心底极不愿看到的。在此,我不由得想起孔子评价《韶》所用的标准:“尽善矣,又尽美矣。”(《八佾》)此等标准,于我实在是可望不可及。如果同仁及读者能够大体认可此书,作为编者,我也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