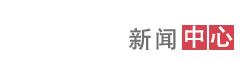冯康
独立创造了有限元方法,自然归化和自然边界元方法,开辟了辛几何和辛格式研究新领域。中国现代计算数学研究的开拓者。生于江苏南京,少年时代家居江苏省苏州,原籍浙江绍兴。
科学家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星宿,而是在人间的凡人,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培养和锻炼,逐渐成长起来的。作为冯康的亲人,我正好有机会得以就近观察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的成长过程,特别是从小学到大学这一阶段。目前素质教育得到社会的大力提倡,冯康的事例对此也有启发。冯康深厚的文化素质要归功于中学教育。他的母校,有名的苏州中学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家庭角度来说,主要是提供了宽松的学习环境,一种氛围。“宽松”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和当今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的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过程从不横加干涉或插手其间,更不施加任何压力。兄弟姐妹之间,虽有切磋之乐,却从不包办代替。记得冯康刚进初中时,英语遇到困难,由于他在小学一点英语也未学过,而其他同学大多学过英语。问题之解决完全靠他自己的努力,很快就跟上了班,不仅如此,还跃居班上的前列。整个这段时期之内,他是轻松愉快地进行学习,而不是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的苦学,从来不开夜车(这和他后来的情况完全不同),即使考试时期,亦是如此。当时的中学教育强调“英,国,算”作为基础,这里稍加介绍。
苏州中学是省立中学,英语限于课堂教学,毫无口语的训练。他课堂英语学得不错,而且还注意到课堂外的自学,在高三期间,常将《高中英语选》上的一些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我记得一篇幽默文章“闺训”曾发表于杂志“逸经”,另有一篇剧作“月起”,则未发表。抗战初期学校图书馆被炸。他曾在断瓦残垣之间、灰烬之中拾得一本英语残书——《世界伟大的中篇小说集》,他就津津有味地阅读其中的一些篇章,这是他阅读英文书刊的开始。英文报纸和电影也成为他学习英语的辅助手段。后来他曾在许多国际会议上用流利的英语作报告并和外国学者交流。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英语口语训练,靠的是中学课堂教学的底子,以及后来的多看多用。至于其它外语,他的俄语受过专门训练,又在苏联住过几年;德语是大学里学的第二外语,可以顺利阅读书刊;法语是自学的,文革后期还用一套唱片学法语会话。总的来说,他的外语素养是非常突出的,不仅能看狭义的科学文献,而且可以在广泛领域来阅读与科学有关联的著作,涉猎极广,如科学家的回忆录、传记、史料与评述等,使他广阅世面,眼界开阔,因而对科学的见解高超过人。另一方面,文化的滋润也给他坎坷的生涯中带来了慰籍和乐趣。记得在1944年他卧床不起,前途渺茫之际,他从阅读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的原文中得到了安慰,他大段朗诵其中的诗句与独白,我至今仍忘不了他在重庆沙坪坝的斗室之中深有感触地用英语朗诵,“让受伤的鹿去哭泣哀号,无恙的野兔嬉闹耍玩,有的该守夜,有的该睡觉,——世道就是如此运转。”他从英文中读莎士比亚与吉朋,从俄文中读托尔斯泰,从德文中读茨威格,从法文中读波德莱尔,原汁原汤,当别有滋味。由此涤荡心胸,陶冶情操,开拓视野,使他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仍然屹然挺立。
谈到中文,他也根底良好。在中学里文言和白话都教,但以文言为主。他能用浅近的文言来写作。记得在文革后期,无书可读,他就买了一套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来消遣。很显然,他的语文素养也在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冯康的科学报告,乃至于讲课,均因语言生动精炼,逻辑性强,深受听众欢迎。他的文章和讲义,也都反映了这一特点。
至于数学,不仅课堂学习成绩优异,他还参考原版的范氏大代数等国外教本进行学习和解题,应该说他中学数学根底非常扎实。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本科普著作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在高三时期,他仔细阅读了朱言钧著的“数理从谈”。朱言钧(朱公谨)是我国前辈数学家,曾在哥廷根大学留学,回国后在上海交大任教。这本书是通过学者和商人的对话来介绍什么是现代数学(其中也提到费马大定理、哥德巴赫等问题),这本书有很强的感染力,使冯康眼界大开,首次窥见了现代数学的神奇世界,深深为之入迷。据我观察,这也许是冯康献身数学立志成为数学家的一个契机。当然,道路并不是笔直的。
冯康的大学生涯一波三折,受到人们的关注。正如Lax教授所述“冯康的早年教育为电机工程、物理学与数学,这一背景微妙地形成他后来的兴趣。”点出了相当关键的问题。作为应用数学家而言,工程和物理学的基础是至关重要的。冯康的经历可以说是培养应用数学家的最理想的方式,虽然这并不是有意识的选择与安排,而是在无意中碰上的。1938年秋他随家迁至福建,有半年在家中自学,读的是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1939年春去僻处闽西北邵武的协和学院数理系就读。1939年夏又考上了中央大学电机系。这可能和当时的时代潮流有关。电机工程被认为是最有用的,又是出路最好的。当时学子趋之若鹜,成为竞争最激烈最难考的系科。他也有青年好胜心,越是难考的,越想要试一试。另外,大哥冯焕(他是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生)的影响也可能是一个因素。这样他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大电机系。入学之后逐渐感觉到工科似乎还不够味,不能满足他在智力上的饥渴感。于是就想从工科转理科,目标定为物理系。由于提出的时间过迟,到二年级尚未转成,就造成并读两系的局面,同时修习电机系与物理系的主课。结果是负担奇重,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此时脊柱结核已初见征兆。从有益方面来看,这样一来他的工科训练就比较齐备了。在三、四年级,他几乎将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全部主要课程读完。在此过程中,他的兴趣又从物理转到数学上去了。值得注意的是40年代正当数学抽象化的高潮(以Boubaki学派为其代表),这股潮流也波及中国大学中有志数理科学的莘莘学子,他们存在不切实际的知识上的“势利眼”,理科高于工科,数学在理科中地位最高,而数学本身也是愈抽象愈好。冯康之由工转理,从物理转数学,而且在数学中倾向于纯粹数学,正是这种思潮的体现。他在学科上兜了一个圈子,对他以后向应用数学方向发展,确有极大的好处。试想当初如果直接进数学系,虽然也要必修一些物理课程,由于上述的心理障碍,必然收效甚微,物理如此,更何况工程了。当前拓宽大学专业的呼声又甚嚣尘上,冯康的事例对此可以给予一些启迪。
冯康在大学读完不久,以脊椎结核发病,由于无钱住院治疗,就卧病在家。1944年5月到1945年9月,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在病床上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现代数学的经典著作,由我亲自经手向中大图书馆借阅Springer出版的黄皮书,数量不少,十几本,就我记忆所及,有Hausdorff的集合论,Artin的代数学等,此外还有市面买得到的影印书,如Weyl的“经典群”,Pontryagin的“拓扑群”等。冯康昼夜沉溺其中,乐此而不疲,使他忘却了切身的病痛和周围险恶的环境。这种数学上的Liberaleducation,既进一步巩固基础,并和当代的新发展前沿衔接起来了,使他对现代数学的领悟又上了一个台阶。1946年夏,伤口居然奇迹般地愈合,能站起来了,随后他到复旦大学任教,他仍坚持不懈地自学。
从1947—1957年这相当于一般人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的阶段。1947年初,冯康到清华大学任教之后,就不再是一个人的自学了,参与了数学的讨论班,先后受到陈省身、华罗庚等名家的教诲。1951年到苏联Steklov研究所进修,他的导师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Pontryagin。受到这么多数学大师的亲自指点,确实是极其难得的机会。这段时期内冯康也发表一些论文如“最小几乎周期拓扑群”等,表明他具备进行数学研究的能力。留苏回来后,又将注意力集中在广义函数理论上,因为物理学家习用德耳塔函数,电机工程师习用运算
冯康-深厚的文化素养
科学家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星宿,而是在人间的凡人,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培养和锻炼,逐渐成长起来的。作为冯康的亲人,我正好有机会得以就近观察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的成长过程,特别是从小学到大学这一阶段。目前素质教育得到社会的大力提倡,冯康的事例对此也有启发。冯康深厚的文化素质要归功于中学教育。他的母校,有名的苏州中学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家庭角度来说,主要是提供了宽松的学习环境,一种氛围。“宽松”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和当今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的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过程从不横加干涉或插手其间,更不施加任何压力。兄弟姐妹之间,虽有切磋之乐,却从不包办代替。记得冯康刚进初中时,英语遇到困难,由于他在小学一点英语也未学过,而其他同学大多学过英语。问题之解决完全靠他自己的努力,很快就跟上了班,不仅如此,还跃居班上的前列。整个这段时期之内,他是轻松愉快地进行学习,而不是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的苦学,从来不开夜车(这和他后来的情况完全不同),即使考试时期,亦是如此。当时的中学教育强调“英,国,算”作为基础,这里稍加介绍。
苏州中学是省立中学,英语限于课堂教学,毫无口语的训练。他课堂英语学得不错,而且还注意到课堂外的自学,在高三期间,常将《高中英语选》上的一些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我记得一篇幽默文章“闺训”曾发表于杂志“逸经”,另有一篇剧作“月起”,则未发表。抗战初期学校图书馆被炸。他曾在断瓦残垣之间、灰烬之中拾得一本英语残书——《世界伟大的中篇小说集》,他就津津有味地阅读其中的一些篇章,这是他阅读英文书刊的开始。英文报纸和电影也成为他学习英语的辅助手段。后来他曾在许多国际会议上用流利的英语作报告并和外国学者交流。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英语口语训练,靠的是中学课堂教学的底子,以及后来的多看多用。至于其它外语,他的俄语受过专门训练,又在苏联住过几年;德语是大学里学的第二外语,可以顺利阅读书刊;法语是自学的,文革后期还用一套唱片学法语会话。总的来说,他的外语素养是非常突出的,不仅能看狭义的科学文献,而且可以在广泛领域来阅读与科学有关联的著作,涉猎极广,如科学家的回忆录、传记、史料与评述等,使他广阅世面,眼界开阔,因而对科学的见解高超过人。另一方面,文化的滋润也给他坎坷的生涯中带来了慰籍和乐趣。记得在1944年他卧床不起,前途渺茫之际,他从阅读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的原文中得到了安慰,他大段朗诵其中的诗句与独白,我至今仍忘不了他在重庆沙坪坝的斗室之中深有感触地用英语朗诵,“让受伤的鹿去哭泣哀号,无恙的野兔嬉闹耍玩,有的该守夜,有的该睡觉,——世道就是如此运转。”他从英文中读莎士比亚与吉朋,从俄文中读托尔斯泰,从德文中读茨威格,从法文中读波德莱尔,原汁原汤,当别有滋味。由此涤荡心胸,陶冶情操,开拓视野,使他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仍然屹然挺立。
谈到中文,他也根底良好。在中学里文言和白话都教,但以文言为主。他能用浅近的文言来写作。记得在文革后期,无书可读,他就买了一套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来消遣。很显然,他的语文素养也在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冯康的科学报告,乃至于讲课,均因语言生动精炼,逻辑性强,深受听众欢迎。他的文章和讲义,也都反映了这一特点。
至于数学,不仅课堂学习成绩优异,他还参考原版的范氏大代数等国外教本进行学习和解题,应该说他中学数学根底非常扎实。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本科普著作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在高三时期,他仔细阅读了朱言钧著的“数理从谈”。朱言钧(朱公谨)是我国前辈数学家,曾在哥廷根大学留学,回国后在上海交大任教。这本书是通过学者和商人的对话来介绍什么是现代数学(其中也提到费马大定理、哥德巴赫等问题),这本书有很强的感染力,使冯康眼界大开,首次窥见了现代数学的神奇世界,深深为之入迷。据我观察,这也许是冯康献身数学立志成为数学家的一个契机。当然,道路并不是笔直的。
冯康-宽广的专业基础
冯康的大学生涯一波三折,受到人们的关注。正如Lax教授所述“冯康的早年教育为电机工程、物理学与数学,这一背景微妙地形成他后来的兴趣。”点出了相当关键的问题。作为应用数学家而言,工程和物理学的基础是至关重要的。冯康的经历可以说是培养应用数学家的最理想的方式,虽然这并不是有意识的选择与安排,而是在无意中碰上的。1938年秋他随家迁至福建,有半年在家中自学,读的是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1939年春去僻处闽西北邵武的协和学院数理系就读。1939年夏又考上了中央大学电机系。这可能和当时的时代潮流有关。电机工程被认为是最有用的,又是出路最好的。当时学子趋之若鹜,成为竞争最激烈最难考的系科。他也有青年好胜心,越是难考的,越想要试一试。另外,大哥冯焕(他是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生)的影响也可能是一个因素。这样他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大电机系。入学之后逐渐感觉到工科似乎还不够味,不能满足他在智力上的饥渴感。于是就想从工科转理科,目标定为物理系。由于提出的时间过迟,到二年级尚未转成,就造成并读两系的局面,同时修习电机系与物理系的主课。结果是负担奇重,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此时脊柱结核已初见征兆。从有益方面来看,这样一来他的工科训练就比较齐备了。在三、四年级,他几乎将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全部主要课程读完。在此过程中,他的兴趣又从物理转到数学上去了。值得注意的是40年代正当数学抽象化的高潮(以Boubaki学派为其代表),这股潮流也波及中国大学中有志数理科学的莘莘学子,他们存在不切实际的知识上的“势利眼”,理科高于工科,数学在理科中地位最高,而数学本身也是愈抽象愈好。冯康之由工转理,从物理转数学,而且在数学中倾向于纯粹数学,正是这种思潮的体现。他在学科上兜了一个圈子,对他以后向应用数学方向发展,确有极大的好处。试想当初如果直接进数学系,虽然也要必修一些物理课程,由于上述的心理障碍,必然收效甚微,物理如此,更何况工程了。当前拓宽大学专业的呼声又甚嚣尘上,冯康的事例对此可以给予一些启迪。
冯康在大学读完不久,以脊椎结核发病,由于无钱住院治疗,就卧病在家。1944年5月到1945年9月,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在病床上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现代数学的经典著作,由我亲自经手向中大图书馆借阅Springer出版的黄皮书,数量不少,十几本,就我记忆所及,有Hausdorff的集合论,Artin的代数学等,此外还有市面买得到的影印书,如Weyl的“经典群”,Pontryagin的“拓扑群”等。冯康昼夜沉溺其中,乐此而不疲,使他忘却了切身的病痛和周围险恶的环境。这种数学上的Liberaleducation,既进一步巩固基础,并和当代的新发展前沿衔接起来了,使他对现代数学的领悟又上了一个台阶。1946年夏,伤口居然奇迹般地愈合,能站起来了,随后他到复旦大学任教,他仍坚持不懈地自学。
冯康-一个数学家成长的道路
从1947—1957年这相当于一般人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的阶段。1947年初,冯康到清华大学任教之后,就不再是一个人的自学了,参与了数学的讨论班,先后受到陈省身、华罗庚等名家的教诲。1951年到苏联Steklov研究所进修,他的导师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Pontryagin。受到这么多数学大师的亲自指点,确实是极其难得的机会。这段时期内冯康也发表一些论文如“最小几乎周期拓扑群”等,表明他具备进行数学研究的能力。留苏回来后,又将注意力集中在广义函数理论上,因为物理学家习用德耳塔函数,电机工程师习用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