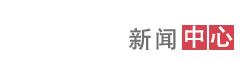文德斯谈舞蹈及3D电影《皮娜》

作者: 凯特·戴姆林
通过《皮娜》一片,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将舞蹈的3D体验带上了大银幕。影片具有全然不同的新维度,尽管在2009年6月30日、即3D的拍摄彩排前两天,皮娜·鲍什(Pina Bausch)令人遗憾地离开了我们。文德斯并没有就此放弃这一计划,而是鼓励皮娜的舞蹈团队与摄制组一起继续完成影片,并以此向皮娜及其表演艺术视野致敬。
闪耀于去年秋的纽约电影节的《皮娜》,12月起在美国诸多影院公映。ARTINFO在电影节期间得以与文德斯深谈,涉及皮娜的创作对他的意义、他最初对舞蹈的兴趣的缺乏、以及他为何差一点就放弃执导这部影片。
ARTINFO:3D效果给人以相当生动的感受。您是否认为这与我们面对现场演出的感受相比,是一种更加亲密的体验?
文德斯:这确实会让人处于一种优势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众就仿佛可以隐身了、可以几乎在室内随意走动,有时坐在第一排、有时在第六排——皮娜本人总是坐在第六排;有时又仿佛可以直接置身台上。这些是在室内的情况,我们此外也有在剧场之外拍摄的部分:这时摄像机就可以与艺术家们一起舞蹈。在舞台上,我们确实试图完全尊重编舞意图以及角度。皮娜是为观众创作了这些作品的,提供的是透视的与正面的视角,而我们多少也遵从了这一规律。有时我们会将视角置于偏左或偏右的位置,试着找到作品每一时刻所对应的理想空间位置,不过我们从未篡改过编舞设计本身。只有当我们得以带着摄像机到户外、到城市中或者在一片风景中时,我就可以自由地360度观看这些舞蹈,这又是截然不同的工作了,因为忽然多了地平线的加入、又有了另一种景深。
ARTINFO:请告诉我们,皮娜的创作对您意味着什么?在看到她的《穆勒咖啡馆》之前,您是否就已是现代舞爱好者了?
文德斯:不,我不能说自己当时就是舞蹈的爱好者。我曾看过传统的、现代的舞蹈,但并未真正被哪一出所打动过。1985年夏天在威尼斯的那一晚,我最初也不没有那么乐意去看《咖啡穆勒》与《春之祭》的联演,在我的女朋友提议去剧场时,我还竭力反对、甚至建议她独自去看,最后还是让步了,心里还是认定这会是一个无聊的夜晚。然而最终证明了这是一段改变我生命的经历。自第一分钟起、以至于整个晚上,我都想着自己正处于某种人生的重要经历中。这是一个我以前所不了解的领域,我不知道还有这样美丽、真是且具有存在感的东西会存在。当时是一次回顾性展演,我们留在威尼斯看了所有的演出,包括了皮娜的六部作品,之后我便前去与她会面。我可以说,这真是改变我生活的时刻之一。
ARTINFO:您最初的计划是拍摄一部关于舞蹈的影片,在皮娜去世后重新对其进行规划一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您是否对如何着手进行这部影片有清晰的想法?
文德斯:并没有。当时我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取消这部电影,无法再进行了。如果说我们花了二十年时间才最终得以开始这部影片,那也等得太久了。于是有人电话告诉我皮娜去世的消息的那天,我给所有投资人、联合制片人以及整个摄制组打电话,要取消这部影片的拍摄。当时我觉得不可能再继续了,因为这确实是我和皮娜两个人共同的项目,必须有她出现在摄影机前后。而那些舞者们都很有热情:甚至在我们获知皮娜过世的那一晚他们还在台上跳舞,尽管是边哭边跳,因为他们都意识到皮娜希望他们这样做。那之后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决定仍作为一个团队继续这个项目,并且尊重皮娜为这部影片所作出的投入,在此后的三年里,各种巡回或演出中他们都遵守并继续了既定的时间表。很自然地,两个月后,他们便开始排练皮娜为拍摄这部影片所规划的剧目。正是在这一时刻,我才意识到取消这部影片是个多么糟糕的决定,而或许也将是这些剧目最后一次被演出。谁知道呢?而皮娜仿佛还在注视着每一位舞者。她曾亲自执导过其中一些年轻舞者排练。我渐渐明白了,我们得继续这部影片。但当然了,这原本必然会是相当不同的一部电影,与皮娜一起制作影片的原计划相当不同;而现在就变成了,我与那些舞者们一起找到一部为皮娜而作、而非与她一起创作的影片。
ARTINFO:皮娜以其与其团队的合作创作而知名。那些舞者也与您一起合作重新规划这部影片么?
文德斯:完全是如此。他们当时仍处于震惊中,当我们完成了拍摄的第一步、即四个小章节的完整拍摄后,我们中间谁都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因此便中断了几个月直至春天,我们也借此开始仔细思考。我经常与他们碰面,经常去乌珀塔尔(Wuppertal)向他们展示影片,我们开始自问如何拍摄一部如此情境下的影片,因为已经有了四部舞剧,却还不是一部电影。渐渐地我们意识到只需要根据皮娜工作的方式来继续,而我从未与她共处过任何完整的剧目创作过程,并不了解她的工作过程,这时那些舞蹈艺术家们便向我描绘他们是如何做的,描绘皮娜是如何为每一出舞剧发展出一系列疑问式的对话的——包括各种个人的、私密的或是综合的问题。她向每个人发出不同的问题,而他们只被允许以舞蹈、以肢体运动的方式来回答她。
我越多地了解到他们所经历的这些过程,我就越来越意识到这便是我们继续这部影片的方式。我也开始发问,而这些问题当然都是关于皮娜的;而我的问题同时也是他们不再能向皮娜发出的问题。尤其是些关于皮娜的眼睛的问题,关于她与他们工作的方式的问题。既然我并非编舞者,我不得不请他们不再通过皮娜所要求的即兴表演的方式来回答,而代以提炼自他们与皮娜之间不可思议的对话的东西——那些皮娜的眼睛所得见的东西、他们曾一起创作出的东西。每个人都向我展示了他们的回答,之后我得以——略似皮娜那般——整理这些回答所组成的可观素材。我试图为他们每个人各选择一个对答,以期这些回答从整体上能勾勒出一幅皮娜的肖像、同时又不至于互相混淆、互相重复得太厉害。而只是在这时,在我们了解到每个人的答案后,我才重新开始拍摄。
ARTINFO:于是这些舞者们都以舞蹈的方式回答了您的问题?
文德斯:是的。
ARTINFO:可他们同时也用言语回答了,在您拍摄他们的面孔时通过画外音的方式。
文德斯:最初并非如此。这儿我需要解释一下,因为当我们开始这部影片时,我很确信将要拍摄一部没有言语的影片,完全没有。与皮娜在一起,我们的计划是要制作一部没有任何采访的影片。首先,没有传记成分——皮娜并不关心这个,也并不想——;其次,没有任何采访的内容。我向她保证过,而我自己也对拍摄一部她的传记影片并没有兴趣,——或许有一天有人会这么做?我深知皮娜对语言文字有多么不信任,也知道对于她而言、接受采访有多么痛苦。她确实接受过采访,尤其在一些巡回演出时,然而在所有这些采访面前——我全都看过了——,我们都能感受到,她清楚知道,若是她开始谈论自己的工作、开始阐释它们,她便背叛了它们。
然而我确是与每位舞者谈论过他们与皮娜的关系。他们对我说自己参与某一出剧、是由于皮娜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创作了它,以及诸如或这是他们首次与皮娜合作、或这已是合作20年后忽然某一天意识到皮娜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等等……我与他们每个人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也用一台小机器拍了下来,却完全没有将这些画面用在影片中的意图。直到我开始剪辑时,发觉若是仅有音乐与舞蹈,整部影片会显得有些……有些隐晦。我并不是想为那些皮娜的粉丝来制作这部影片,而尤其是想要为那些对皮娜的创作不太熟悉的人——那些像在看到任何一部皮娜作品之前的我一样的人,那些认为舞蹈并不是给自己看的人——来完成这一一部电影。于是我意识到影片需要一些背景,需要让人了解这样的创作是如何发生的,于是也就需要人们在影片里谈论皮娜。我记得这些谈话,我记录下他们每个人的话,然后为几乎每一位舞者都找到了一段话或几行字,我请他们依据这些再重新录音,以他们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录音文字。接着我们将这些声音构成的肖像与那些沉默的面孔放在一起。这就是这些想法进入影片的方式。
ARTINFO:皮娜与您都属于二战中或是战后诞生的一代德国人,您是否觉得这也在你们之间建立起某种艺术上的关联性?
文德斯:嗯,一定有。我们都说着带莱茵兰(Rhineland)口音的德语,皮娜从未抛弃过这种地方口音。我们的家乡相隔不到50公里。我对乌珀塔尔也比较了解,因为小时候经常去那儿坐那种悬轨车,我也了解它周遭的风景。而更关键的是,当我看了她的创作、当我与她见面后,我认识到她确是像我的一位姐姐,一位我从未有过的姐姐,我们都有过同样的在沙漠一般的战后德国成长的经历。乌珀塔尔曾被摧毁,就像我住过的杜塞尔多夫一样,这些城市都曾有80%以上被战火毁灭。我们都出生在这种无人之地般的地方,与生俱来都带有一种被表达出的对身在别处、以发现其他世界、其他开放性的渴望。这是我们所真正共享的东西,远甚于其他。我想,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舞剧时也同时感受到的东西,我感到自己理解这种语言,我的骨头、我的身体都能理解这种语言。甚至是皮娜处理音乐的方式也让我感到熟悉。全然是全新的,却又立即熟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