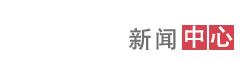虚拟技术

我在手机里养了一些鱼,有些是白鳍橙色的,有些背上有黑点,它们在海水中游动,背景是苍白平坦的沙子,有一些岩石,还有鲜绿色的水草。有时候它们游出屏幕外,我就瞪着空荡荡的背景,意识到它们很快会游回来。当我轻轻触碰屏幕,水面就荡漾起一片涟漪,鱼儿就游开了。这是一种动态手机屏幕墙纸,手机里有个水族馆的想法让我很高兴。
1984年,精神病学家亚伦·卡特丘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团队,在繁忙的牙医候诊室里做了一个实验。有些日子,研究者在诊所放了水族箱,里面有一些热带鱼。另外一些日子,他们把水族箱拿走了。他们在两种不同环境下,测量了病人的紧张度,结果很明显。有水族箱的日子,病人不怎么紧张,更配合手术。卡特丘得出结论,色彩丰富的鱼类对即将接受牙科手术的人起到安抚作用。1990年,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朱迪思·赫尔瓦根发现,在牙科诊所悬挂大型的描绘大自然的壁画,能起到水族箱一样的安抚作用。2003年,德克萨斯州A&M大学的环境心理学家罗格·乌尔里奇发现,假如室内播放录有大自然声音的磁带,等待献血的志愿者就会血压降低,心跳减缓。
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花时间凝视手机虚拟水族箱?最简单的答案是否定。卡特丘的鱼是真实的,我的只是动画。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管“自然”环境是真是假,我们的反应非常类似。研究表明,即便是模拟的自然,作用也十分明显。2008年,西班牙巴斯克大学的哈特曼和阿保拉萨对伊维尔德罗拉公司的新电视品牌营销进行了调研。该公司希望营造“绿色”的形象,所以在推广中运用了许多大自然风光,比如飞翔的老鹰、绵延的群山和飞流直下的瀑布。研究人员发现,消费者不管是不是关心环境问题,都对新品牌产生好感。视觉模拟迎合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渴望,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效应。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在真正的自然变得越来越稀少,而生活越来越虚拟化的情况下,虚拟自然可以代替真实的“绿色产品”。
但是,对我们来说什么是“自然”呢?这个名词似乎总是带着一种浪漫与感伤的色彩。当我们说起“回归自然”,仿佛大自然是被人类干涉与糟蹋了,而在此之前有一个纯净的自然。美国诗人和环保主义者加里·斯奈德在 《荒野实践》中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大自然”的定义。他说,一种是户外的“物质世界,包括所有生物。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是指人类文明和意志的产物之外的世界。机器、人工制品、装置或不同寻常的东西(比如双头牛)都是"非自然"的。”
另一种定义更加宽泛,包括了所有人类行动和意愿的产物。斯奈德称之为物质世界及其所有物体和现象。他写道:“科学和某些神秘主义认为所有东西都是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纽约城、有毒废弃物,还是原子能,都不是"非自然的",没有任何我们在生活中所做和所经历的事情是"非自然的"。”这当然包括技术产品。斯奈德更喜欢这个定义,我也一样。
从2004年开始,我开始收集计算机文化中经常出现的自然隐喻和形象—比如,“流”、“云”、“病毒”、“蠕虫”、“冲浪”、“域”等等。我希望从人类、信息空间和大自然之间的交集中能发现什么。
在这样一个时代,自然和技术越来越相互依存,而不是成为竞争对手。我由此制造出一个新词“technobiophilia”,意思是对“技术和生命的热爱”,这是个复杂难懂的词,也许并不确切,但这就是如今正在发生的。对技术和大自然同时的热爱,使我们在这个数字的世界里生活得更好。
因此,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把虚拟现实和自然世界分开,比如,关掉机器、远离电脑、戒掉网瘾,来亲近大自然,而是把这一切看做完整的世界里不可缺少的综合元素。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为了在数字世界中生活得更好,我们必须把虚拟世界跟大自然联系在一起,在设计中体现更多自然元素和对大自然的热爱。这样,我们才能把脚下的地球跟电脑中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相关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