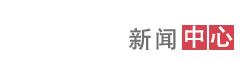3D技术时代的媒介延伸与感官重构
一、“重返部落”与3D虚象
尽管源自于偏光原理的三维立体显示技术早在上世纪初即已问世,人们对于立体电影一词也逐渐耳熟能详;但直到2010年初《阿凡达》的横空出世之后,3D才正式以铺天盖地的气势宣示了一个时代的来临。高速度渲染、CG以及液晶同步、圆偏振等新技术的成熟运用,让以往困惑于色差和清晰度的3D视像制作及观赏有了质的飞跃。《阿凡达》所展现的神奇世界和震撼的视效场景,直接触发了新一轮的3D热潮。跟风之作的接踵而来和各类3D电视的营销造势,以及3D频道在全世界范围的纷纷开设,皆向我们表明,技术范畴的3D已经演化为一种新兴媒介,开始全面融入日常消费和娱乐生活。3D视像在视觉层次和空间维度的纵深扩大,无疑再一次为我们“打开了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①如就感知结构和环境营造方面而言,阿凡达式的经典虚拟世界以我们能触及的方式再次诠释了海德格尔所谓技术对“自然、现实和世界的构造”。
全方位立体景观的呈现和对人感官神经的近距离冲击,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去理解五十余年前麦克卢汉带有预言性质的时空图景描述:“我们今日的加速度并非缓慢的从中心向边缘的外向爆炸,而是瞬间发生的内向爆炸, 是空间和各种功能的融合。我们专门化的、分割肢解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文明, 突然又将其机械化的碎块重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而且这一重组又是瞬间完成的。这是一个环球村的世界。”②3D图景所映照的环球村,既是对现有真实世界在二维延伸之后更立体完美的再现,同时也是一个不同于二维平面的独立世界的理想再造。
如果说电视是人的各种感觉器官的全面延伸的话,那么照此而论,3D媒介则是感觉器官的延伸综合,是更名副其实的整体延伸。在这一媒体世界当中,人的三维感知结构得以更真正的实现,如果辅之以当下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则理想中“整合的部落网络里人们相互依赖,所有的成员都生活在和谐之中”③这样的场景将指日可待;人的整体融合亦即麦氏所云“重返部落”的时代即将来临。
然而,我们有所疑问的是,在此对世界的延伸和再造过程之中,3D视效的逼真固然使得人们浑然迷醉,近在咫尺和宛在身旁的感觉亦进一步“悬置”了媒介的工具性,让幕布和机器皆退隐其后;但在借助媒介对世界的三维再现过程中,传播内容与个人接受之间能否建立起更贴近、更真实的对应关系?诚然,一如麦克卢汉对媒介和语言的相关论述,当媒介工具凸显了人的精神而非遮蔽它之时,即神似于“语言越流畅,我们越是意识不到语言的存在”④这样的境界之时,现象学观照和“得意忘言”的主体领悟的确可以引领人们修复“理性的分裂”。
但3D视像对媒体的介质性到底是有所融化还是彻底遮蔽?和平面电视、广播等传统的电子媒介相比,当媒体内容的接受以身体在场的形式与自我进行交流的时候,在此崭新的媒介生态环境当中,自我主体究竟是走向解放从而回归部落时代,还是被另一世界空间完全湮没从而陷入“自己的幻象”(鲍德里亚),将是我们面临3D虚象所须深思的问题。
二、新感知革命:视觉触觉的分合之辨
虽然阿凡达以视觉“奇观”效果为主要卖点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并创造了新的票房神话,但其更为深远的影响却是这种全新感受背后所蕴含的复杂媒介意义。3D在空间维度上的拓展使得个人长期以来基于平面介质上的感官经验发生了巨大转变。
根据本雅明和巴赞的观点,如果说摄影与摄像是在平面上对现实进行的机械复制和完整展现,那么3D则是在超越平面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再现世界的方式。麦克卢汉曾认为印刷时代对视觉功能的偏重造成了人主体感官整体性的分裂,而电子时代的来临以视听融合的方式重新宣召了个体感官的整体回归,电视首先结束了“视觉独霸地位”。尽管对此豪泽尔曾以剧场和伴奏舞蹈为例进行反驳,并认为“电视所带来的电影亦基本如此变化只能说明视觉功能的胜利,而不是失败。”⑤而我们反观今日所谓“图像世界”对自身的重重包围时亦发现,铺天盖地的各色符号、图案与活动影像的“视觉霸权”地位甚至更胜以往。
但3D媒介对观看方式的改变,却在这个后电子时代恰到好处的提醒我们,麦克卢汉对声觉-触觉空间到视觉空间转换过程的论述似乎并不是个简单的悖论,相反,却可能正是对感官延伸走向的另一角度的启发,并且隐隐透露出电子媒介对感官凸显和整合的总体趋势。虽然麦克卢汉时代对电视延伸触觉的观点是建立在低清晰度图像的基础上,而今天围绕我们的是越来越纤毫毕现的高清影像,但这一过程却以看似背道而驰的角度重新诠释了“一切感官最大限度互动”⑥的深层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数码显像和光学还原等技术完善后出现的3D媒介,正是视觉独霸和触觉延伸的双向碰撞焦点。如今,当电视电影观众无一例外都已从“屏幕”变为“摄影机”的时候,3D视像恰恰正体现出这种视觉延伸到达顶峰后的转向寓意。从再现和感知方式上来看,它完全突破了长久以来的平面感官经验,但从生理本质而言,却又无法脱离视觉功能这一基本的感官限制。故而,3D媒介的勃兴和盛行,其本身所兼具的二重特性将我们正式引到了感官平衡和感官迷失的分岔路口,同时亦预示着新一轮“感知革命”⑦的开始。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自身感官对身外世界把握的限度一直是久论不息的问题,进入文字时代之后,对身体和理性的自觉思考逐渐让视觉和触觉成为感官理论思辨的重点。正是基于对自我主体的观照,前苏格拉底时代对视觉和触觉的认识就已呈现出两相对立的趋势。柏拉图对视觉有距离的论述和亚里士多德灵魂论中触觉基础的观点,实质上直接开启了后世的视觉中心主义和身体经验等诸多内容。随着现代工业化的推进,外在媒介对人类社会和生理感官的影响也逐渐成为社会哲学和技术哲学反思的重心。从黑格尔、海德格尔到梅洛庞蒂以及从芒福德、英尼斯到麦克卢汉,我们看到的是对理性和异化不断深入的探讨,也是对视觉和触觉的分合之辩。从一方面来看,作为今日视觉显像技术的顶峰,3D媒介无疑是“最抽象、最易于骗人的视觉”⑧的极致,“景观社会”在3D的助推下似乎让视觉全面代替了其他感觉。
但当我们置身于3D视像之中时却发现,恰恰正是这种极致的视觉景观,首次以具象的方式让视觉经验和“身临其境”的整体感知达成了最紧密的重合;身体触感欲望在视觉功能的范畴中反而得到了隐隐调动和激发。就形而上层面来说,正如德里达所言,“既是理论的(视觉中心的)又是"触觉中心的"(haptocentrique)哲学与某种被文化标识了的"身体"经验有关。”⑨在新媒体文化时代的今天,我们的身体经验正是在视觉世界中逐渐被建构和解构,3D在对视觉感觉向纵深扩展的同时推动了身体知觉的前进。从这一点来讲,与本雅明所说的触觉转向不同的是,3D环境的立体逼真对触觉的本初地位产生了复醒作用。如前文所言,如果说麦克卢汉就电视的低清晰度来论述观众其他感官的调动是一种被动参与姿态的话,那么3D视像对感官参与则是高度仿像下的主动强烈诱发。
以此而论,随着图像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3D媒介无疑带来的将是进一步的多感官共同互动,是麦克卢汉所说的触觉延伸在当代的最佳注释。从另一方面来看,3D建立了新的显像方式和观看方式,并正在渗透改变叙事方式;但无可置疑是,现阶段3D视像的显示载体依然是平面幕板,其感官接受的生理机制也依然是视觉感光。我们通过观看所建立的三维立体世界,从本质上来说,实际是大脑中枢神经的强制错觉。以《阿凡达》所代表的典型看,其更多还是对技术的展示与夸耀,如圆偏振、液晶同步开关等“先进”的3D眼镜,以及热烈造势下3D电视的“视听盛宴”,无不透露出单方面消费欲望的急功近利。具体考察不难发现,现阶段3D效果远胜往日的成功,实际是建立在对更庞杂的制作、观看设备的依赖之上。
从媒介理论而言,今天的3D媒介实际上是媒介之中的媒介。在特殊摄影机、观影眼镜和特殊放映屏的层层阻隔之下,大脑视觉神经的长时间被迫移位和强制幻想,将扭曲正常的视觉功能;而同时出现的如眩晕、呕吐等身体感官反抗性的应激,又将阻断视觉与触觉的延伸和共生。从这点来说,70年代苏联曾研试的全息立体电影的展现方式,倒是对3D发展有一定的启发。
三、3D时代感官审美的新变化与设限
在视觉文化及奇观理论盛极一时的今天,3D媒介带来了新的展现“世界存在”的方式,但其首先震撼和改变的是我们最直接的感官体验;视觉和触觉的新变化带来了感官审美的新变。就观看方式而言,3D对视觉习惯的改变与视觉理论的诸种言论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对照。麦克卢汉在论述媒介建立感知时,曾引证非洲土著人看不懂电影的材料说明我们具有欧几里德空间和“三维的或透视的眼光”;本雅明谈论艺术也曾对视觉的“凝神专注”和触觉的“消遣休闲”作了区分。
在3D影像的观赏过程中,此二者几乎被全部打破和搅碎;透视角度不复存在,我们不再如以往般对电影凝视或消遣,而是 “与客体完全融为一体”,3D让我们的眼光如非洲土著一样掠过,甚至如他们一般在观看中“眼睛也用,但不是用来透视,而是仿佛用来触摸”。⑩电视的听觉-触觉性质在此演变成为视觉-触觉性质。因此,今日我们对3D媒介的审美把握,与其说是视觉文化语境下的虚实之论,无宁说是身体感知在视觉基础之上的审美距离重建。
正如劳拉·马科斯根据德勒兹“光学影像”所提出的“触觉性视觉”概念,11光学变化关系使得保持距离的视觉让位于触摸,再次构想客体被间距离观看;在视觉距离几近消除的3D影像中,“触觉性视觉”让我们重新感知客体对象的存在性。因而,在此基础上3D的审美走向,应当更进一步以构筑涉身知觉与视像的融入互动为重心,在制造视觉“震惊”(本雅明)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视觉之外的身体感官的经验记忆和想象距离,以更直击的方式唤回人们心灵深处“看”的完整性;即德里达所说的“作为视觉特权真正目的的触觉特权”。
故此,当下3D视像的审美维度之论,在过多涉及视觉热点及下辖的情节设置问题之外,还应针对上述感官审美路径来对影像制作和展现重心进行有效设限,从而将3D引向良性循环而不是走向批判技术和高举人文的简单对峙。单就审美而言,与前文字时代不同的是,3D媒介对受众参与的调动是否定之否定式的往复,在更多媒介的参与下,麦克卢汉给我们描绘的“重返天堂”时代也许并非虚言。
注释
①⑥⑩麦克卢汉等:《麦克卢汉精粹》[M], 何道宽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1 页,第246页,第200页。
②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31页。
③纪莉:《论麦克卢汉传播观念的“技术乌托邦主义”》[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
④魏敦友:《回返理性之源》[M],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184页。
⑤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M], 居延安译,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264页。
⑦殷晓蓉:《网络传播文化:历史与未来》[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39页。
⑧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M],张宁译,三联书店,2001年,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