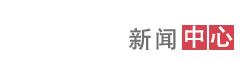曾昭抡
经费;二要保证教师的业务时间。要求大力改善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条件,切实解决好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问题。
曾昭抡认为,要提高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必须要提高教材质量和师资质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材和教学方法也要不断更新。他在实践中努力体现这一教育思想。为了制订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大纲,他亲自抓典型,经常深入到学校的教师、干部和学生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与大家平等的交换意见和看法。
曾昭抡很重视高等学校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副主任,每年都认真组织审查高考试题,并亲自撰写有关高考的指导性文章。他非常重视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他说:“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培养学生的政治质量、教学质量和身体健康水平三方面。”在教学质量方面,他还强调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特别是对那些出类拔萃的学生,要加以重点培养和扶植。
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曾昭抡还十分热心我国的科学事业。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和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这时他已经兼任20多个职务,他抽出时间并认真做好每一项兼职工作。例如他经常到科学院化学所主持工作,参加会议。他善于了解情况和倾听知识分子的意见,既注重发挥老科学家的专长,又强调发挥青年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努力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1957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开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曾昭抡作为民盟中央常委和其科学规划组的召集人,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
为了解决当时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曾昭抡和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经过调查和座谈,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关于保护科学家,关于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业务部门的研究机关之间的分工协作,关于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和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光明日报》在1957年6月9日发表了这份报告,并加了“互相监督,开拓新路”的短评,予以推荐和称赞。
这个报告指出了当时在我国科技体制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些办法和建议。例如,针对一些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提出要协助他们妥善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针对科学院、高等学校和工业部门之间存在本位主义,提出了合理使用人力和协调彼此关系的建议;针对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和留学生时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倾向,提出了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等建议。
曾昭抡主持起草的这份报告,与后来我国制订的《科研工作十四条》、《高教工作六十条》等科学、教育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见他们是有远见卓识之士。然而这些宝贵意见在当时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批判。
为了帮助党整风,当时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召集民盟中一些知名学者、教授开了一次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在会上谈了一下大鸣、大放开始后个人所接触到的情况以及对形势的一些看法。这六位教授很快就被划为大右派,成为重点批判和讨伐的对象。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六教授。”
曾昭抡从进步教授到领导干部,忽然间又成了大右派,许多人都感到惶惑不解。在批判曾昭抡的会上,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材料,有人便特意去找他的学生唐敖庆,让唐揭发他的问题。唐敖庆说:“我不能揭发我的恩师,因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当让唐敖庆写揭发曾昭抡的书面材料时,唐敖庆实在无奈,只好写了一份他从1936年入北京大学化学系至1950年留学回国这一段时间与曾昭抡接触的历史。他写了与曾昭抡参加步行团、由长沙到昆明的情景;曾昭抡在西南联大认真讲课、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积极搞民主运动而深受学生敬佩的情况,以及曾昭抢教授带他们到美国去留学的情况。这哪里是揭发材料,简直是回顾师生之情的赞歌,它也充分体现出唐敖庆这位正直无私的科学家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
曾昭抡工作勤奋、待人和气,虽身居领导岗位,但毫无官架子。在教育部工作时和他接触过的一些人,包括他的秘书、警卫员和勤杂工都对他十分尊重,并为他被划为右派和撤销副部长职务而感到十分惋惜。
曾昭抡被划为右派后并没有悲观失望,但撤销职务、停止工作却给他带来莫大痛苦。南开大学杨石先校长十分理解曾昭抡的心情,曾两次给校党委打报告,提出要曾昭抡到南开大学工作,但未能得到如愿的答复。1958年4月,他应武汉大学李达校长之邀,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此时,他已年近花甲。虽然因做行政方面工作而脱离教学第一线多年,但又有机会回到熟悉的讲台和实验室,直接为国家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事业贡献力量,而使他异常兴奋。
曾昭抡到武汉大学后,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从早到晚在图书馆、资料室如饥似渴地查阅文献资料。他经常对年轻的教师和学生说:“图书资料是前人工作十分宝贵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主要依据。”“图书馆是我们学习工作的重要场所。要经常查阅图书资料,熟悉各种专业期刊的内容、特点和查找方法,甚至在哪个书架、哪一层都要熟悉,这样查起来又准确又方便。”曾昭抡在武汉大学除了上讲台、实验室外,其余时间大多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患高度近视,但查阅资料的速度却异常惊人,像小跑似的在书架丛中穿梭,很快就抱出一大摞书,几乎是不依靠视力查找。查阅后又以同样速度迅速归还原处,然后又抱出一摞。他这种专心致志做学问的精神,给学生、教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样不管是严寒酷热的天气,还是风雨泥泞的道路,他总是每天去的最早、走的最晚的一个。盛夏的武汉奇热无比,到图书馆去的师生,都希望坐在电风扇旁边,而去得最早的曾昭抡却坐在远离电风扇的地方,把好位子留给别人。严冬,他总是穿着单薄的棉袄,戴着一顶褪了色的旧帽子,看书时经常打冷颤,甚至流清鼻涕,但他仍是那样专心入神,别人问他:“曾先生不冷吗?”他说:“
曾昭抡认为,要提高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必须要提高教材质量和师资质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材和教学方法也要不断更新。他在实践中努力体现这一教育思想。为了制订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大纲,他亲自抓典型,经常深入到学校的教师、干部和学生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与大家平等的交换意见和看法。
曾昭抡很重视高等学校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副主任,每年都认真组织审查高考试题,并亲自撰写有关高考的指导性文章。他非常重视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他说:“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培养学生的政治质量、教学质量和身体健康水平三方面。”在教学质量方面,他还强调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特别是对那些出类拔萃的学生,要加以重点培养和扶植。
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曾昭抡还十分热心我国的科学事业。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和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这时他已经兼任20多个职务,他抽出时间并认真做好每一项兼职工作。例如他经常到科学院化学所主持工作,参加会议。他善于了解情况和倾听知识分子的意见,既注重发挥老科学家的专长,又强调发挥青年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努力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蒙受不白之冤
1957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开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曾昭抡作为民盟中央常委和其科学规划组的召集人,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 为了解决当时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曾昭抡和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经过调查和座谈,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关于保护科学家,关于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业务部门的研究机关之间的分工协作,关于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和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光明日报》在1957年6月9日发表了这份报告,并加了“互相监督,开拓新路”的短评,予以推荐和称赞。
这个报告指出了当时在我国科技体制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些办法和建议。例如,针对一些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提出要协助他们妥善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针对科学院、高等学校和工业部门之间存在本位主义,提出了合理使用人力和协调彼此关系的建议;针对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和留学生时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倾向,提出了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等建议。
曾昭抡主持起草的这份报告,与后来我国制订的《科研工作十四条》、《高教工作六十条》等科学、教育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见他们是有远见卓识之士。然而这些宝贵意见在当时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批判。
为了帮助党整风,当时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召集民盟中一些知名学者、教授开了一次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在会上谈了一下大鸣、大放开始后个人所接触到的情况以及对形势的一些看法。这六位教授很快就被划为大右派,成为重点批判和讨伐的对象。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六教授。”
曾昭抡从进步教授到领导干部,忽然间又成了大右派,许多人都感到惶惑不解。在批判曾昭抡的会上,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材料,有人便特意去找他的学生唐敖庆,让唐揭发他的问题。唐敖庆说:“我不能揭发我的恩师,因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当让唐敖庆写揭发曾昭抡的书面材料时,唐敖庆实在无奈,只好写了一份他从1936年入北京大学化学系至1950年留学回国这一段时间与曾昭抡接触的历史。他写了与曾昭抡参加步行团、由长沙到昆明的情景;曾昭抡在西南联大认真讲课、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积极搞民主运动而深受学生敬佩的情况,以及曾昭抢教授带他们到美国去留学的情况。这哪里是揭发材料,简直是回顾师生之情的赞歌,它也充分体现出唐敖庆这位正直无私的科学家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
曾昭抡工作勤奋、待人和气,虽身居领导岗位,但毫无官架子。在教育部工作时和他接触过的一些人,包括他的秘书、警卫员和勤杂工都对他十分尊重,并为他被划为右派和撤销副部长职务而感到十分惋惜。
晚年无私奉献
曾昭抡被划为右派后并没有悲观失望,但撤销职务、停止工作却给他带来莫大痛苦。南开大学杨石先校长十分理解曾昭抡的心情,曾两次给校党委打报告,提出要曾昭抡到南开大学工作,但未能得到如愿的答复。1958年4月,他应武汉大学李达校长之邀,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此时,他已年近花甲。虽然因做行政方面工作而脱离教学第一线多年,但又有机会回到熟悉的讲台和实验室,直接为国家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事业贡献力量,而使他异常兴奋。 曾昭抡到武汉大学后,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从早到晚在图书馆、资料室如饥似渴地查阅文献资料。他经常对年轻的教师和学生说:“图书资料是前人工作十分宝贵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主要依据。”“图书馆是我们学习工作的重要场所。要经常查阅图书资料,熟悉各种专业期刊的内容、特点和查找方法,甚至在哪个书架、哪一层都要熟悉,这样查起来又准确又方便。”曾昭抡在武汉大学除了上讲台、实验室外,其余时间大多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患高度近视,但查阅资料的速度却异常惊人,像小跑似的在书架丛中穿梭,很快就抱出一大摞书,几乎是不依靠视力查找。查阅后又以同样速度迅速归还原处,然后又抱出一摞。他这种专心致志做学问的精神,给学生、教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样不管是严寒酷热的天气,还是风雨泥泞的道路,他总是每天去的最早、走的最晚的一个。盛夏的武汉奇热无比,到图书馆去的师生,都希望坐在电风扇旁边,而去得最早的曾昭抡却坐在远离电风扇的地方,把好位子留给别人。严冬,他总是穿着单薄的棉袄,戴着一顶褪了色的旧帽子,看书时经常打冷颤,甚至流清鼻涕,但他仍是那样专心入神,别人问他:“曾先生不冷吗?”他说:“